近日,文學院李永東教授撰寫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解放”書寫》在《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7期)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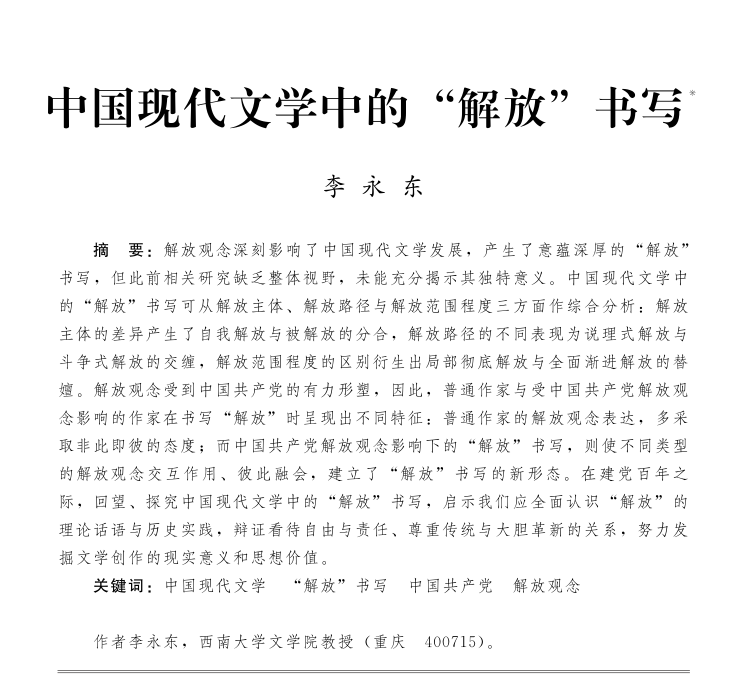
摘要:解放觀念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產生了意蘊深厚的“解放”書寫,但此前相關研究缺乏整體視野,未能充分揭示其獨特意義。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解放”書寫可從解放主體、解放路徑與解放范圍程度三方面作綜合分析:解放主體的差異產生了自我解放與被解放的分合,解放路徑的不同表現為說理式解放與斗爭式解放的交纏,解放范圍程度的區別衍生出局部徹底解放與全面漸進解放的替嬗。解放觀念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有力形塑,因此,普通作家與受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的作家在書寫“解放”時呈現出不同特征:普通作家的解放觀念表達,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態度;而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下的“解放”書寫,則使不同類型的解放觀念交互作用、彼此融會,建立了“解放”書寫的新形態。在建黨百年之際,回望、探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解放”書寫,啟示我們應全面認識“解放”的理論話語與歷史實踐,辯證看待自由與責任、尊重傳統與大膽革新的關系,努力發掘文學創作的現實意義和思想價值。
關鍵詞:中國現代文學 “解放”書寫 中國共產黨 解放觀念
作者簡介:
李永東,1973年生,湖南永興人,西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約150篇,30余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轉載。出版《租界文化與30年代文學》《租界文化語境下的中國近現代文學》《文化間性與文學抱負》《民國城市的文學想象與民族國家觀念》等6部專著。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其他項目多項。曾入選2019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曾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2015年度中國人文社科最具影響力青年學者,重慶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次),重慶市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重慶藝術獎等獎勵。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7期P63—P87
“解放”作為一種極富感召力和建構力的觀念,貫穿于現代中國的整個歷史過程。解放觀念不僅構成了現代中國的重要歷史面向和思想流脈,而且作為一種具有統合性的觀念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這種影響既體現為不少現代作家就是解放思潮的助推者和引領者,也體現為現代文學作品容含了豐富復雜的解放觀念,還體現為現代文學通過解放的方式尋求自身的嬗變。而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觀念對現代文學中的“解放”書寫產生了巨大影響,形成了嶄新的書寫形態。
在“解放”這一概念下,聚集著諸如個性解放、女性解放、家庭解放、階級解放、民族解放等諸多類別,所有這些解放類別幾乎都與中國現代文學有密切關聯。由此,從各種解放類別出發來研究現代文學,便成為學界的普遍選擇,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成果主要從單一的解放類別出發來審視現代文學,缺乏整體觀照的視野,存在明顯的碎片化傾向。而且,學界對單個類別的解放觀念與現代文學關系的研究,常截取某一時段的現象進行考察,缺乏歷時性和整體性的梳理、比較與評析。尤其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中國共產黨是現代中國解放觀念的制造主體,幾乎每種類型的解放觀念都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有力形塑,現代中國的各大解放思潮最終也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建構中得到匯集和升華,進而形成內蘊獨特且影響深遠的解放觀念。現代中國諸種解放觀念被中國共產黨征用改造或發展完善的具體過程,無不映射到中國現代文學的演進風貌中,這是以往分散式、截段式的研究路徑難以洞悉的。有鑒于此,本文選擇以整體性的解放觀念來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將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觀念作為論述重點,進而運用比較方法,厘清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及其影響下的作家創作之于中國現代文學“解放”書寫的獨特意義。受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的作家,主要指那些具備黨員身份的文人,如茅盾、蔣光慈、郭沫若、夏衍、丁玲、田漢、周立波、柳青等;或當時雖無黨員身份但卻是黨領導下的重要文化骨干,“左聯”、延安、解放區作家是其中的三大群體。這些作家的“解放”書寫承載了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的豐富意涵和重要經驗。除此以外的作家,本文視為普通作家。將普通作家與中國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作家的解放觀念、“解放”書寫進行參照論述,可以呈現現代文學“解放”書寫的整體風貌,也有助于揭示出中國共產黨如何引導、豐富現代文學的解放觀念和書寫形態。
一、“解放”釋義與“解放”書寫的面向
“解放”可以說是現代中國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晚清時期,“解放”一詞已零星出現于知識分子筆端。1919年前后,“解放”一詞的使用頻率突飛猛進,并出現了以“解放”命名的雜志,如《解放與改造》《解放畫報》。之后,“解放”的使用頻次有所回落,但言說解放、分析解放的文章依然蔚為可觀。借助瀚堂近代報刊數據庫進行全文檢索可發現,從1871年到1949年,使用“解放”一詞的文獻共47931篇,使用“自由”“平等”“民主”這三個詞的文獻分別為502627篇、42444篇、74338篇。與這三個詞的使用頻次相比,“解放”的使用頻次并不占明顯優勢。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解放”的角度來把握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這是因為,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系列關鍵詞,如革命、反帝、反封建、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等,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納入“解放”的范疇,它們或可被視為解放的路徑、對象,或可看作解放后的應然狀態,共同詮釋了現代中國的解放之路。然而,對解放的認識,人們通常著眼于政治、社會層面,對其復雜內涵認識不夠,缺乏宏觀、整體的考察視野。
在現代中國的革命實踐、思想演進和文學書寫中,“解放”意為解除個體或群體遭受的種種壓迫和束縛,使之獲得自由發展、平等對待的可能。然而,由于解放主體和客體的多樣性,解放方式和解放范圍程度的差異及解放的目標指向(個人、性別、階級、民族、國家等)和連帶觀念(自由、平等、獨立、科學等)的豐富性,解放的表意便向整個現代中國歷史和文學敘事敞開,其內涵和外延大大拓展,成為一個統合性的思想觀念。
現代知識分子在談論解放時,常把解放與自由聯系在一起。實際上,近代中國最初時興的觀念為自由、平等,直到新文化運動后,解放的觀念才大范圍傳播,正所謂“昔日自由今解放”。沈雁冰在《五四運動與青年們底思想》一文中也提到,辛亥革命后,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觀念是“自由”“平等”,而五四運動后,則流行的是“解放”“改造”。由于解放指向人對自由之境的渴望,因此,“五四”以后解放觀念與自由觀念便如影相隨:“解放就是恢復自由。”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也常論及解放與自由的關系。陳獨秀認為,“解放就是壓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別名”。毛澤東自20世紀20年代始,即把解放和自由看作革命目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6年,他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文中指出,依托于工人階級的國內階級戰爭,才是“解放人類”,實現“人類真正的平等自由”的途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前后,毛澤東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和史沫特萊的談話》《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矛盾論》等文中,反復強調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與解放。抗戰時期,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任務出發,主要從兩個維度詮釋了解放與自由的關系:一是提出新三民主義,強調“對外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兼顧了民族和人民的前途;二是根據抗戰形勢的發展,明確了黨的斗爭目標為“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對解放與自由關系的理解,影響了文學中解放觀念的構成及“解放”書寫的風貌。
自由是主體獲得解放后的一種應然狀態,反過來,自由作為一種愿景,會預先對解放的操作性方案提出要求。首先,自由存在著外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差異。其中,經濟物質等外在的壓制束縛較好識別,從中解放出來較易獲得共鳴,破除此類外在障礙的解放之舉可以采取外部激勵、引導乃至命令等方式。與之不同,精神文化層面的內部桎梏則不大容易被人發現,所以要獲得精神層面的自由便顯得困難重重,精神的解放只能采取積極主動的方式而不是被動等待的方式。總之,面對精神的抑或實體的束縛壓迫,主體追求的自由境界存在內外之別和虛實之分,相應的解放行為便具備了對內與對外、針對實體與面向虛設、借助外力與堅持自主的多重指向。大體來說,普通知識分子通常更看重解放對內、向虛的一面,當他們認識到民眾的落后面貌時,便將自己看作解放民眾精神的實施主體;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則是內外結合、虛實互補的,在面對民眾的思想缺欠時,旗幟鮮明地強調“待解放者”主體自覺自動的必要性。正是在這種多維度指向的解放邏輯上,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受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的文學創作,呈現出豐富的解放圖景,留下了不少值得認真借鑒和深入討論的“解放道路”與“解放書寫”。
其次,主體對自由的追求,存在徹底與漸進、全面與局部的分別,這進一步規約了解放的操作路徑和解放的范圍程度。對有的人來說,解放是大膽擺脫一切外在束縛,追求無拘無束無掛礙的自由狀態。在此情況下,求取解放的過程必然對武力的革命性舉動青睞有加,解放的態度堅決徹底、激進。而在另一部分人看來,解放的真諦主要是朝向內在和自我,它意味著破除自身思想的因襲和精神的拘囿,以求主體的良性發展。相應地,施行此類解放時,理性啟發、思想引導是相關人士選擇的主導方式,他們以長遠、穩健的態度對待解放和自由的展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解放選擇,主要作用于國人的思想精神內部,把個人從禮教、迷信、奴性等觀念的禁錮之中拯救出來,可稱之為啟蒙式解放;后來的革命者采取的解放策略主要針對專制、殖民、侵略等外部壓迫因素,以反帝、反封建、反資本主義作為行動指南,可類比為革命式解放。不過,當我們仔細辨析那些深受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的作家的“解放”書寫時,就會發現:武力斗爭與思想引導這兩種解放路徑存在交錯互滲的趨勢,思想精神解放與經濟社會解放幾乎受到了同等對待。徹底與妥協、激進與平穩這兩種本來判然兩別的解放態度,實際上并非完全對立,二者的交互關系呈現出的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一個壓倒另一個的模式,而是革命式解放邀約啟蒙式解放、啟蒙式解放推動革命式解放的復雜形態。
此外,自由還有群體自由與個體自由的分殊,與之相對應,解放便會形成群體解放與個體解放的差別。現代中國因長期處于屈辱狀態,加之革命風潮的強勢助推,因而群體自由常占據主導地位,群體解放也總是對個體解放進行監督和指引。五四文學重在個人的解放和自由,用沈雁冰(茅盾)的話說,就是“解放了伊,做個‘人’!”而其后的中國共產黨倡導和革命作家表現的,則重視群體的解放和自由。不過,在群體解放召喚群體自由的時代話語背后,個體解放引領的個體自由時時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解放的具體操作實踐的不同階段,需要處理不同的問題,進行不同的抉擇。從邏輯的先后來看,解放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開啟解放,此時的重點是確立以誰作為解放的實施主體。如果把“待解放者”視作解放的實施主體,就需要“待解放者”能認識到自身被壓迫、受束縛的遭遇,進而爆發出主動求解放的意愿和行動;反之,則是把他人當成解放開啟時的實施主體,進而從外部對“待解放者”進行詢喚、啟發和教導。中國現代文學的“解放”書寫在解放主體這一層面,大致經歷了從理想化的自我解放,到現實性的被他人解放,再到20世紀40年代的自我與他人、革命者與民眾之間互為解放主體的演化情形。
明確了解放的實施主體之后,緊接著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落實解放,此時需要處理的問題是決定以何種方式和路徑展開解放的過程。一般而言,要么是以說理的方式,向壓迫者講述自身的悲慘遭遇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使對方認識到癥結所在;要么是以革命手段,推翻壓迫者長期以來的強勢地位。在解放路徑這一層面,五四文學的“解放”書寫熱衷于以說理啟蒙的方式展開,左翼文學多強調革命斗爭敘事,20世紀40年代黨領導下的文學“解放”書寫則注重說理和斗爭密切配合。
實施解放行動后,又需要從范圍和程度兩個維度來規劃、規約解放,由此就呈現出局部徹底解放與全面漸進解放之分。在解放的范圍層面,五四文學的解放聚焦于思想,左翼文學關注階級壓迫和經濟解放,而兩者在解放程度上都主張徹底;與之相比,20世紀40年代黨領導下的文學的“解放”書寫則全面鋪開,大大增加了解放的包容度,又能根據實情策略性地推動解放進程。解放的三個階段面臨的三組對應關系,即自我解放與被解放、說理式解放與斗爭式解放、局部徹底解放與全面漸進解放,帶來了中國現代文學“解放”書寫的主要差異,而在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下的作家對解放的書寫,恰恰較為辯證地處理了每一階段的每一組對應關系,因而彰顯了自身的獨特價值。
作為一種思想觀念,解放指涉不同的對象,“解放誰”的問題顯得至關重要。因為解放對象的不斷更新,中國現代文學先后形成了女性解放、個人解放、家庭解放、階級解放、民族國家解放等解放類型的書寫。解放對象的演進歷史,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解放”書寫的主要邏輯線索。現代中國的解放言說,最初聚焦的對象為女性。據筆者查閱的材料,第一篇冠名“解放”的文章,為1907年在《天義報》連載的《女子解放問題》。該文從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維度來使用“解放”一詞。“五四”前后,在個人主義、反叛傳統的時代聲浪中,女性解放和個人(或個性)解放的言論尤為密集,成為當時中國解放“大家族”中的最強音。女性解放的最終指向是“叫婦女來做個‘人’”,即“肉體上的束縛和精神上的束縛”都獲得解放的個人。由此,五四時期的女性解放與個人(或個性)解放就構成了彼此呼應、相互促進的關系。在文學中,光彩照人的“娜拉”便成為叛離家庭、求取解放的典型形象。胡適的《終身大事》開其端,廬隱的《海濱故人》、歐陽予倩的《潑婦》、茅盾的《創造》等作品緊隨其后,都可以說是對“娜拉”的謳歌。而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作家在五四時期則更側重對個性解放的書寫。
無論女性解放還是個性解放,往往都把家族制度的壓迫當作應破除的首要對象。因此,家庭解放也成為五四文學“解放”書寫的重要一脈。從陳獨秀1915年提出“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的口號后,家庭解放言說便充滿了激進的判語。這些說法既是當時人們對家族制度貽害過重產生強烈反叛心理的流露,也是魯迅所說的與其“開窗”受阻不如索性“拆屋頂”的策略性表態。正因此,現代作家在書寫家庭解放時的矛盾、徘徊心態更值得我們關注。這種心態在魯迅的雜文、小說的互文性寫作中獲得了深切表現。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娜拉走后怎樣》等經典雜文中,寄望于覺醒的父母能秉持利他、犧牲的態度,“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以便達到“平和而沒有沖突”的良好效果。然而,魯迅小說中的那些“父親”依然堅守傳統規矩,從《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到《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再到《長明燈》中的“瘋子”,那些覺醒的子女,均深陷入理性想掙脫家庭的圍困而情感又顧慮重重的兩難境地。雜文魯迅與小說魯迅的參照,展現了既得“隨順長者”又要“解放幼者”的家庭解放難題。
五四時期的女性解放、個人解放和家庭解放的觀念接受和文學書寫,就其實際而言屬于知識青年的自我解放,且偏重于精神、欲望的解放。普通作家盡管明了經濟對解放的根本作用,但在文學書寫中還是側重精神、欲望的解放,不斷重復接受新觀念、自由戀愛、反禮教、反家長權威的“解放”書寫模式。沒有獲得現實社會支持的精神解放,其文學書寫的價值在于喚醒、發現“人”,但作品中的自我解放者往往陷入夢醒后卻無路可走的境地,新生的自我承受著更大的生的苦悶。像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呈現的就是追求解放的女性在精神、欲望上的苦悶。可以說,五四時期普通作家的“解放”書寫,表現的不是解放后的自我飛揚,而是“解放的苦悶”,找到了反抗壓迫的入口,而暫時未找到自由與解放的出口。這與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觀念和實踐既提供入口又提供出口形成了鮮明對比。
“五四”落潮之后的土地革命時期,社會改造和社會革命的呼聲愈發嘹亮。順應這種變化,文學的“解放”書寫也展現出新面影。女性解放、個人解放匯入社會解放和改造的時代潮流中,現代作家進而表達了對女性參加革命斗爭的期許。蔣光慈的小說、茅盾的《蝕》三部曲等是對將女性解放納入社會革命斗爭的具體寫照。家庭解放也在革命的號召下變得更為徹底。巴金的《家》就通過覺慧逃離家庭走向社會的進程,反映了封建大家庭在激流勇進的社會革新思潮中搖搖欲墜的情形。蔣光慈的《田野的風》等作品的解放態度更為決絕,賦予了家庭與革命判然兩別、互不相容的色彩。與此同時,有關階級解放的文學書寫開始大量涌現。茅盾的《子夜》按照階級分析觀念書寫中國的社會構成,在勞資沖突、民族資本家與買辦的斗法中暗示了階級和國家解放的路徑和方向。夏衍的《包身工》從壓迫的系統性敘述中昭示解放之路,系統性的壓迫包括資本代理人對紡織女工的壓榨,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掠奪,這造成了紡織女工的悲慘命運,而階級解放和民族國家解放的主題隱含其中。土地革命時期的文學“解放”書寫,尤其是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的創作視野更為宏闊,開始擺脫五四文學沉湎于精神、欲望的解放而忽視社會斗爭的缺陷。
在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兩大觀念先后統攝一切。受此影響,文學的“解放”書寫又一次展現出轉變的痕跡。接續已有的女性解放思路,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從階級維度豐富了女性解放書寫的內涵。以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為例,折聚英這個“過去的難民”“過去的童養媳”“過去的文盲”“過去只值兩斗粗谷子的女人”,在黨的引導和幫助下,成長為“學習的模范”“勞動的英雄”“抗日的戰士”“婦女的先鋒”。革命感召下的此類底層婦女,成了“最好的婦女徹底解放的榜樣”,有力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對現代文學女性解放書寫的內涵拓展和強力導引。在抗戰動員的語境中,家庭解放與民族國家的前途緊密掛鉤,文學敘事也“開始了‘家國同構’的重建”。面對戰時的民族國家危機,知識分子倡導家庭解放主要是為了抗戰的需要,因為“抗戰就是把各個人由家庭里抽出來,編到社會國家里去”。值得辨析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也主張把個體從家庭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但其家庭解放并不是從外部打碎舊家庭進而使個體走向群體;相反,而是更強調從思想上對個體進行開導,進而在內部重塑家庭面貌,取得內外共生的深層次解放效果,這在趙樹理的《傳家寶》、傅鐸的《王秀鸞》等作品中都有充分體現。這是家庭解放復雜性的折射,也是特別需要留意的解放經驗。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階級解放書寫中,丁玲和趙樹理的相關創作無疑最具代表性。以此二人的書寫為中心,聯系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解放論述,參考前后不同作家的創作,可以洞察到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觀念及其影響下的文學“解放”書寫,是如何辯證對待解放開展的階段性和多維性的。
從解放對象的歷史變遷中,可以看出普通作家與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作家在解放觀念的面向上是有區別的。這些觀念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具體化為對解放的主體、路徑與范圍程度的繁復表現,從中可洞悉“解放”書寫的豐富性,尤其是發掘出中國共產黨對“解放”書寫的觀念引導和模式開拓。
二、解放主體:自我解放與被解放的分合
解放觀念落實為解放行動,首先需要確立由誰來實施解放,即解放的實施主體問題。外力的刺激、推動和幫助,帶給受壓迫者的解放屬于被解放,他人是解放的實施主體;反之,受壓迫者識別壓迫處境,積極抗爭的行為則是主動解放,自我是解放的實施主體。解放主體的不同連帶出自我解放與被解放的區別。中國現代文學對這兩種解放的書寫,經歷了由分到合的過程,形成了三個階段。五四文學中的知識分子雖然是解放觀念的傳布者,但他們深感外來的解放思想不能讓民眾真正領會和認同,于是便熱切呼喚民眾勿待他人來解放自己,而要努力做到自我解放。自我解放的期許落到實處,既會面臨傳統思維習慣和生活習性的妨害,也會遭遇文化守成主義者的批駁,其反響往往因此比較冷淡。五四時期自我解放的理想化吁求收效不大,而后的激切革命解放思想洶涌而來,緩慢的自我解放便更受冷落。到了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大力倡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方針,知識分子與民眾得以緊密交匯,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開始意識到革命者與普通民眾彼此隔膜的問題,于是在書寫解放運動時,他們便極為注重讓革命者解放民眾與民眾自我解放相配合。此時,需要解放的就不只是普通民眾,革命者與知識分子也必須在解放浪潮中接受洗禮,因此,革命工作者與普通民眾之間交互擔起了解放主體的角色。
五四知識分子是各種解放觀念的熱烈鼓吹者,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也對宣教式的解放路徑表示不滿,期待知識青年在態度和行動上主動尋求解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陳獨秀、李大釗就曾大力倡導“自己解放自己”。陳獨秀指出:“解放重在自動,不只是被動的意思,個人主觀上有了覺悟,自己從種種束縛的、不正當的思想習慣迷信中解放出來,不受束縛,不甘壓制,要求客觀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自動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義。”李大釗更斬釘截鐵表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在五四文學中,多有關于自我主動解放的書寫。郭沫若的詩歌《天狗》《鳳凰涅槃》無疑是表現自我大解放的篇章。魯迅的小說《孤獨者》《傷逝》和郁達夫的小說《沉淪》中的知識青年,在保守勢力和世俗偏見的壓抑、圍困中,尋求自我意志和生命解放,他們的掙扎、頹廢甚至絕望亦是對自我解放的悲壯注腳。
五四時期的主動解放屬于知識分子的自我解放,盡管在觀念言說和文學書寫上多把“大眾”“平民”視為解放的主體,但實際上更多是一種理念虛設。可以說,自我主動解放的呼聲雖然動聽,卻多少帶有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因為普通民眾可能已對各種壓迫習以為常,很難自動識別壓迫的存在,遑論產生解放的要求進而奮起抗爭。因此,當一位讀者給《解放畫報》去信,聲明“解放,要自己解放自己,他人是愛莫能助”時,編輯在回信中說:“因為有許多人受禮教,制度,習慣,風俗,捆綁已久,他們自己簡直不覺得是束縛,你不替他‘解’,他怎么肯‘放’呢?”然而,由外力來解放他人是需要現實條件配合的,知識分子不顧實際情形想要解放“沒有自立的能力”的柔弱者,有時恰恰事與愿違。比較而言,中國共產黨盡管將民眾視為亟待解放的對象,但由于注意到解放的多重關聯條件,并且注意激發民眾自我解放的意識,因此取得了顯著成效。
發動革命必然“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然而,由于普通民眾身上存在諸多問題,要使農民全身心參與革命解放運動,就必須對其進行教育引導,“須隨時隨地注意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換言之,革命解放需要正視民眾身上存在的弱點,告別縹緲玄遠的自動解放設想,對受壓迫者進行教導,促使解放觀念深入人心,進而產生群體性抗爭舉動。受此影響,革命文學中出現了許多把革命領導者當作解放的實施主體,以之引導民眾響應革命運動的“解放”書寫模式。在巴金表現礦工悲慘命運的小說《萌芽》中,礦工們雖然打心眼里覺得世道不公,但為了生存,“只得裝聾做啞,把壞人也當做好人來尊敬”。遭受冤屈毒打后,屈從甚至自殺成了不少工人的選擇。礦工一面憎恨、一面屈從的狀況,直到革命者文科員走到工人中間宣講革命思想時才大為改觀。文科員的幫助和教導促生了礦工的革命解放意識和行動,使革命的“萌芽”種子開始植入工人思想深處。在蔣光慈《田野的風》(即《咆哮了的土地》,出版時為了躲避檢查,改為此名)中,安于被剝削處境的蒙昧鄉民,同樣是在張進德和李杰等革命者的指導下,才將“蒙蔽的障幕揭去了”,“開始照著別種樣子看待世界,思想著他們眼前的事物”。
在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曾提醒革命者領導農民群眾時,不能“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他指出,革命者不能發號命令,更不能越俎代庖,“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唯有如此,才能取得“引而不發,躍如也”的效果。這一提醒在當時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相反,倒是陳獨秀提出的由知識分子引導民眾的觀點受到一些革命者青睞。陳獨秀認為,“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識有職業的市民”,“群眾心理都是盲目的”。其結果,有的變革者過于強調外力引導的必要性,把革命領導者視作解放運動獨一無二的實施主體,相對漠視被壓迫者自我解放的主體能動性。于是,從理想化的自我解放轉變為更具現實可操作性的被解放時,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革命領導者和普通民眾、解放的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彼此隔膜甚至有些割裂的狀況。
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略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但現代作家仍然多為生活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因此在左翼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革命者作為解放主體來解放他人的書寫模式。丁玲20世紀30年代轉型期的許多作品表現了革命者對解放的引導與掌控,《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美琳獲取解放的方式是受到革命者若泉的感召,《一天》中的革命青年陸祥希望通過“文藝的體裁”啟發工人覺悟,鼓舞他們的斗志。直到全面抗戰爆發,許多作家在遷徙中被迫疏散到大后方的鄉鎮,從而真正走進農民、工人、士兵的生活中,“解放”書寫開始真正貼近民眾,如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郭沫若的《金剛坡下》、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等作品,都觸及了民眾日常的精神、物質困境及由此萌生的抗爭意識和解放訴求。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后,中國共產黨除了繼續主張“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工作方針之外,更強調黨員干部應該“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在教育群眾之前,“首先要改造自己和向群眾學習”。在干部引導群眾與群眾教育干部相結合的思路下,解放的發送者與接受者之間開始拋棄主動與被動的兩分關系,轉而為交互作用、彼此融會、共同提升。由此,從晚清到20世紀30年代以城市的知識分子、革命者、工人為中心的“解放”書寫,讓位于以鄉村的農民和革命者為中心的“解放”書寫,自我解放與被解放也由分立走向了融合,革命領導者與普通群眾呈現出互為解放主體的情形。
革命領導者與普通群眾互為解放主體的書寫,主要體現在延安文學和解放區文學中。丁玲的長篇小說《桑干河上》便一改她前期創作中由他人領導解放的書寫模式,積極探索普通民眾與革命干部相互融會、相互解放的新路徑。一方面,土改工作組的進入,開始打破暖水屯的沉悶狀態,逐漸解決了民眾“了解得太少,和顧忌太多”的問題,逐步掀起了土地改革運動的浪潮。另一方面,土改工作組的不少成員、暖水屯的許多村干部開始時各有各的缺陷,后來在深入群眾運動的過程中,這些人都被群眾翻身解放的強烈愿望和巨大能量所感染,從而糾正了自身的不足。革命者的引導打消了農民的顧慮,這大致屬于被解放的路徑;農民醒悟后產生了強勁的革命浪潮,這可以說是一種新的自我解放形式。通過對這兩種解放路徑的交織書寫,《桑干河上》深刻地展現了自我解放與被解放互補互促的過程。草明的工業題材小說《原動力》同樣表現了領導干部與工人群眾相互作用、相互解放的過程。最初,以老孫頭為主的進步工人,雖然甘于吃苦、沒有私心,但他們還缺乏主宰機器的自信心,后來在上級的教導啟發下,工人們才在階級思想層面以主人翁自居,并爆發出革命智慧和雄心。與此同時,由第一次修機失敗發展到第二次修機大獲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工廠經理王永明等黨的領導干部在民眾的解放浪潮中受到教育、獲得成長。經由這番交互影響與彼此解放的合力作用,小說揭示出所謂的“原動力”是“優秀的工人”與“民主政府的領導”相結合的道理。
自我解放與被解放的路徑差異及其分合,也對解放言說的話語風格和宣傳動員方式帶來深刻影響。對久受壓迫的普通民眾而言,即便他們意識到自身的悲慘處境,但要奮不顧身、起而抗爭,也還面臨諸多障礙,其中之一便是缺乏強有力的話語理論支撐。因為中國鄉村是熟人社會和人情社會,講信修睦,貶抑爭執,尊卑有序。要打破這種狀況,民眾需要一套全新的、權威的話語理論來激勵和支撐,于是,革命道理的宣傳便顯得意義重大。康濯1949年創作的小說《黑石坡煤窯演義》便詳細狀寫了老尹給大三等民眾“解說要訴苦翻心抱團體的一些個道理”,正是這些“道理”使村民找到了斗爭的理據。在康濯的另一篇小說《我的兩家房東》中,農村姑娘金鳳正是從工作隊員“我”講解的“雙十綱領”中,感知到中國共產黨為民做主的光輝形象,了解到中國共產黨關心婦女、維護婚姻自主等政策條文,擺脫了“害臊勁”,勇敢地與“不務莊稼活”“胡鬧壞女人”的未婚夫解除婚約,與進步青年拴柱訂婚。
要使鄉村民眾無畏且順利地追求解放,外力的幫助和指引不可或缺,革命理論話語則是外力的主要體現,由此形成的是被解放的路徑。可是當革命者為民眾提供話語引導和思想啟發之后,如若再滿口高深的理論話語,無視普通民眾的欣賞喜好,就難免生出隔閡。《原動力》中的陳祖庭之所以不被工人擁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一說就長篇大論”。《桑干河上》中的文采喜歡通過開會枯燥地宣講文件上的大道理,致使不少人心生抱怨。有鑒于此,中央宣傳部發文嚴肅批評了群眾宣傳工作中存在的“語言文字的不生動和不通俗”,“方式方法的刻板化和不善于因時因地制宜”等缺點,提醒各地干部在做群眾工作時要盡量利用“民間的通俗的文藝形式”,才能“極力激起群眾的感情”。
以群眾容易理解并接受的形式,助推革命解放運動的展開,這其實就是將被解放的路徑轉化為民眾自我主動解放的路徑。當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工作隊從“開大會”轉變為組織群眾“嘮嘮嗑”時,大家才敞開心扉,分享各自遭受的壓榨經歷。在柳青《土地的兒子》中,村民將李老三翻身解放的真實故事改編為戲劇進行演出,此類“在群眾翻身基礎上隸屬于群眾自己的,歌頌著群眾自己的翻身,有廣大群眾參加”的文娛活動,除了具備感情宣泄的作用外,還最大程度強化了群體的凝聚力和認同性,從而激發起民眾主動要求進步:“舊社會活不成,新社會救咱們!”“共產黨給咱們好日子過的!”“學習李老三,務正生產吧!”正因為宣傳方式與動員群眾的效果密切相關,所以,使用何種方式宣講革命道理,就成為文學書寫中評判不同干部工作能力高低的重要標準。《李有才板話》中的章工作員在發動農民時,采用的是開會講道理的刻板方式,老楊同志來后,則通過快板歌謠充分了解到村里的實情和村民的真實想法。在實際發動群眾過程中,老楊同志堅決摒棄了章工作員的工作模式,利用歌謠號召大家參加農會。《李有才板話》的解放斗爭取得勝利,從宣傳形式上看實乃“板話”的勝利,而“板話”正是民眾自我解放的表征。
歌謠、小調、壁報、說書、戲曲表演等通俗易懂的文藝樣式,因其與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欣賞習性相契合,所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作家筆端被頻繁采用和精心打磨。當廣大民眾深深沉浸于這些文藝樣式時,他們的內心世界被打開,進而主動響應解放征召并爆發出巨大的革命勢能。與此同時,通俗化的語言、受群眾歡迎的形式及身邊真人真事的素材產生了良好的宣傳效果,不僅“打通”了群眾的內心障礙,還攜帶著民眾主動解放的熱情,反過來對革命宣教者的認識進行修正和提升,有力“打通”了干部的經驗認識。《桑干河上》中的劉教員開始辦黑板報時,習慣用“之乎者也”的語言向民眾解釋黨的政治道理,農民老吳對之表達了不滿,并即興編唱了一段朗朗上口的土改歌謠。劉教員在老吳的指點和表演的促動下,終于豁然開朗,懂得了“咱編黑板報是寫給老百姓看呀”的道理,采納老吳的建議,以通俗化的形式重新編寫黑板報。“適應初起的莊稼人的生活方式”的宣教手法,使革命者與民眾“雙向打通”,帶來了“雙重解放”的良好效果。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人與革命作家在延安整風運動后關于階級解放的敘述,既呈現出革命者“說服”“啟發”群眾的過程,還同時展現了群眾“說服”“啟發”革命者的過程,由此,干部由“自動”向“自覺”轉變,群眾則由“被動”向“主動”轉變,最終產生了自我解放與被解放的共振互促的情形。
三、解放路徑:說理式解放與斗爭式解放的交纏
確立了解放實施的主體后,就進入了解放的具體展開過程,在此過程中會面對如何解放,即解放的路徑問題。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采取何種方式實施解放,主要表現為說理式解放與斗爭式解放的路徑差異。說理式解放是指通過話語交流、思想宣傳、觀念引導的方式,讓人們意識到自身所處的被束縛、被壓迫的境遇,從而謀求解放,或是在觀念上已覺醒的人以話語交涉的方式向壓迫者提出自由、平等和被公正對待的解放訴求;斗爭式解放則是通過直接對抗、有力手段、革命行動以擺脫外在的束縛和壓迫,包括群眾自覺進行的斗爭式解放和革命者領導的斗爭式解放。
按理說,解放總是要反抗和推倒特定的壓迫對象。換言之,解放天生帶有某種斗爭性。但晚清和五四時期興起的女性、家庭、教育、個性等解放潮流,幾乎不約而同地采取了說理式解放路徑,并影響到文學的“解放”書寫。魯迅小說的“解放”書寫,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故而多采取說理的方式,《狂人日記》詛咒“吃人”、勸轉“吃人”及呼吁“救救孩子”,可以歸入說理式解放的敘述類型。高歌的小說《生的旋律》采取的也是說理式的構思,在父親的審問與“我”的駁詰中表達了關于家庭解放的主題。說理式解放的文學書寫,在題材上偏重戀愛家庭、學校教育、禮教習俗方面,敘述的重心多落在人物的心理體驗和思想沖突上,表達主旨立意多借用象征隱喻的修辭手法。
五四時期的說理式解放,規避了解放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流血犧牲和暴力凌辱現象,可問題是說理式解放要么難以取得勝利,要么難以維持勝利。巴金在20世紀30年代初創作的《家》,即表明了這個觀念。小說以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作為故事的時代背景,大哥覺新在某種意義上便是說理式解放的踐行者。當覺新為覺民的婚事向祖父說理受到痛罵后,他便順從了。與之不同,覺慧因散發傳單受到祖父批評時,也曾與祖父講過道理。但說理失敗并未讓覺慧屈服,反而使其意識到“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了解的”,由此萌生了叛離的因子。最后,覺慧以逃離大家庭的方式,擺脫了束縛,獲得了解放;覺新則唯唯諾諾在高家繼續煎熬著。有感于說理式解放路徑的虛妄,北京大學的學生費覺天曾提出,以血淚為表現的“力”應成為“自由的代價”。他認為,西方眾多解放容易取得成功是因其具有“力”的庇護,而民國初年的解放極易失敗正是由于缺乏“力”的庇護。言下之意,要想讓解放取得實效,參與者須擁有強大的力量。對費覺天的觀點稍作引申,便是說理式解放很難保證解放的成功和解放成果的延續,要想解放,斗爭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中國共產黨是解放的實踐派和行動派,相信“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因而,革命斗爭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即信奉的解放路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其行動綱領即要求革命作家“站在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的戰線上,攻破一切反動的保守的要素”。嗣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進一步強調“在文學的領域內,宣傳蘇維埃革命以及煽動與組織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斗爭”。
與中國共產黨對革命斗爭的推崇相呼應,斗爭式解放成了左翼作家筆下的革命者堅定執行的革命道路。例如,陽翰笙《歸來》中的革命者,“只知道奔忙,只知道拼命,只知道苦斗,只知道不斷的不斷的向前努力!”蔣光慈《田野的風》里的農會成員,即便被解散被鎮壓,也勇毅地與敵人抗爭,堅信“只有在殘苦的斗爭中才能奪得自己階級的福利!”在左翼文藝思潮影響下,其他作家也形成了斗爭式解放強過說理式解放的觀念。巴金的小說《萌芽》就明確表達了對斗爭式解放的贊許和對說理式解放的否定。小說一方面大力歌頌文科員帶領下的工人堅決與工廠主斗爭的行為,另一方面塑造了一個同情工人處境卻主張和平改革的科員張溫平。在小說結尾,文科員帶領工人沖進了礦局,昂然迎接即將到來的鎮壓軍隊,“萌芽”的種子被倔強的革命者種下。張溫平則帶著妻子離開礦廠,宣告了自己信奉的說理式解放的失敗。
20世紀30年代初期,有的作家以“說理”見長,如丁玲的小說《田家沖》敘述階級解放時,把三小姐作為革命說理的主體,把田家沖的青年作為革命動員的對象,小說重點講述的是階級革命觀念的啟蒙、傳播。有的作家則濃墨重彩地展現了激動人心的革命斗爭場景,然而忽略了對說理式解放路徑的認識和借用。講述單一的斗爭式解放故事的作品,其中的革命領導未能向群眾詳細說明革命的復雜面向,相關情節未能有效展示革命深入且徹底重塑群眾思想的深意。與之不同,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40年代采取的解放路徑及其影響下的革命作家的階級解放書寫,則看重說理式解放的意義,細致敘述了革命道理重塑民眾思想的過程。這尤其體現在表現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的文學創作中。
減租減息運動及土改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行的最具代表性的階級解放運動,兩者雖有程度上的差別,但都特別強調向群眾宣講革命道理,使斗爭成為群眾自覺行動的路徑。中國鄉村的廣大農民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盡管他們從情感上對現實處境感到不滿,但又深受“命運”“良心”等傳統觀念束縛,“不懂得剝削和被剝削的階級關系及其產生的社會根源”。要使革命解放成為群眾自覺主動的行為,首先需要打破群眾思想觀念中的種種顧慮。周而復《山谷里的春天》就是以農民陳五兒轉變落后思想,最終勇敢向地主斗爭的過程為書寫重心,閻爭先等干部反復向陳五兒講解革命道理的過程,則是陳五兒擺脫順服心態、投身解放斗爭運動的關鍵。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運動中,民眾除了被種種傳統觀念禁錮外,還普遍存在“怕變天”的心態。新的“怕變天”心態和舊的“命運”“良心”等觀念的束縛,共同妨害了農民對土改運動的參與。于是,消除農民對“變天”的擔憂,成為階級解放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趙樹理、康濯等作家都曾表現過農民在“怕變天”心態和其他落后觀念的共同影響下,喪失革命反抗決心和毅力的場景。對此,丁玲在1952年出版的《桑干河上》的修改本《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借助農會主任張裕民之口評價說,關鍵是“莊戶主還沒有翻心”。康濯的《黑石坡煤窯演義》也以質問的語氣指出了問題的關鍵:“你們莫非還沒翻心?還是封建大腦?”“翻身”的前提是“翻心”,要成功實現階級解放,前提是通過說理的方式使民眾在思想觀念上獲得解放。“翻身”屬于斗爭式的解放行為,“翻心”則必須采取說理式解放路徑,而算賬和訴苦則是說理式解放兩大行之有效的策略。
算賬是為了“算還自己被剝削了的血汗”,其目的是讓農民明確他們所受的剝削情況,相信革命斗爭的合理性。《山谷里的春天》中的農民被組織起來召開租戶會時,白長成主動出擊,向大家算起了農民被欺壓的苦賬。白長成的一席話活動了村民的心眼,“在大家心坎里勃起勇氣來了”,成功激勵村民說出了“明減暗不減”的真實情況。白長成的算賬屬于面對農民的說理,旨在喚醒農民的反抗意識。當直接面對地主時,白長成那種一對一的算賬形式力量不夠,于是便出現了《桑干河上》中的郭富貴等人與江世榮夫妻的集體算賬場面。集體算賬的形式把江世榮的罪惡集中起來、凸顯出來,讓農民更清晰地認識到地主剝削的殘酷性。
算賬之外,訴苦更是調動農民斗爭意識的有效策略。在《暴風驟雨》中,地主韓鳳岐被扣押后,小說便濃墨重彩地描寫了農民訴說苦楚的場景。群體性的訴苦情緒促使民眾爆發出勇毅堅定的斗爭舉動。類似的訴苦場景在馬加的《江山村十日》、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里也多有表現。訴苦過程以“共鳴”的方式,濃墨重彩地展示和確認了農民的悲慘遭遇,進而最大程度調動了群眾的抗爭意識。對此,《桑干河上》中的宣傳部長章品的概括極為貼切:“咱們如今就是叫大家多想想人家給咱們的苦處,多想想過去的封建社會是怎么的不合道理沒有天理良心。”同時,訴苦不僅是情緒調動的策略,也是政治感召的儀式,它通過引導農民意識到自身的苦難來源于地主的壓迫,最終喚醒農民的被剝削意識,啟發受苦的群眾獲得階級覺悟,“開始向‘階級’認同轉化”。
不論是啟發教導民眾,還是通過算賬、訴苦等獨特方式讓民眾識別壓迫遭遇、獲取革命意識,都證明斗爭式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說理式解放絕不是一件可以馬虎對待的小事。只有通過精心謀劃的說理,消除民眾的思想顧忌,才能使階級解放觀念真正被民眾理解、認同和踐行。正如《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所言:只有當農民“為著自己的利益理直氣壯直接行動起來,相信自己的力量時,問題才能解決得徹底,群眾才能提高一步”。而且,經由一系列的說理而獲得解放的民眾,最后不但會自覺自動地與壓迫者作斗爭,更會在思想深處來一番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說理式解放促發了斗爭式解放,斗爭式解放進一步造就了思想世界的重構。這是傳統思想觀念被黨的革命思想取代的過程,是傳統鄉村社會在革命的沖擊下舊貌換新顏的過程,是劉少奇稱之為“換了一個腦袋”的“新的啟蒙運動”:“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教育農民,是新的啟蒙運動,也就是階級教育。這個教育搞好了,農民跟上我們走,就不會因為受一點波折而懷疑動搖。”
四、解放的范圍程度:局部徹底解放與全面漸進解放的替嬗
在解放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明確了具體展開路徑,還需要定奪解放的范圍和程度,于是有了局部徹底解放與全面漸進解放這兩種情形。解放的范圍有全面與局部之分。全面解放是指破除一切內在和外在的束縛,消除人們在精神與物質上,或政治、經濟與文化上承受的壓迫和不平等;局部解放則是指解放觀念和實踐在精神與物質這二者中,或在政治、經濟與文化這三者中,只取其一,單項突進,不及其他。解放的程度有徹底與漸進之別。徹底解放是指態度激進,追求速效,以完全解除束縛、消除壓迫力量為目的的解放;漸進解放則是指根據現實狀況逐步實施和策略性推進的解放。在現代中國的解放觀念和解放實踐展開過程中,局部解放往往顯得徹底,全面解放反而多取漸進的方式,由此形成了“局部徹底”和“全面漸進”這兩種主導的解放態勢。
晚清的解放觀念及其“解放”書寫,不脫“中體西用”的觀念框架,《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海上塵天影》等小說,基本上秉持“提倡新政制,保守舊道德”的局部解放意旨。傳統倫理道德尤其是家庭倫理觀念,在晚清制約著解放的敞開維度。同時,在列強環伺、國勢岌岌可危的局勢下,以救亡為目的的解放觀念,也表現出決絕的態度。五四時期亦多取局部徹底的解放。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國民的精神思想痼疾是妨礙國家進步的最大障礙,因此徹底反傳統,將思想精神的解放定為主要目標,其他層面的解放則被有意無意忽視了。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解放不再以精神思想解放為主要目標,經濟物質層面的解放凌駕于其他解放之上,相關文學作品聚焦于塑造不妥協、堅決斗爭的英雄人物。徹底解放的思想觀念氣勢恢宏、振奮人心,同樣也有其局限性。之所以出現局部徹底解放的歷史狀況,是由于現代中國的發展采取歷史因素(經濟、政治、文化)單向/單項突進的方式,也就是局部突進的方式,結果使得后一歷史階段不得不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采取同樣激進的“補償式的新拓展”,從而造成了孔范今所說的“歷史結構的悖論性與文學的補償式調整和發展”。這就規約了各個類型的解放也就是局部解放先后發生,并以強烈反撥前一階段解放觀念和文學書寫的方式來推進。
從以器物科技、精神思想為主轉到以經濟物質為主,解放都指向局部性的壓迫束縛。缺乏全局性的視野,極有可能使主體從一個桎梏中解脫出來,卻陷入另一個桎梏之中。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深入理解民眾的前提下廣泛動員民眾,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充分考慮到民眾的生活習性、接受心理和國內的實際情形,并且注重整體解放的可能,然后有針對性、策略性地調整解放思想,使解放運動能以全面漸進的形式落地生根并鋪展開來。以五四時期為例,當時人們的“改造”“解放”觀念是有傾向和選擇的。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主要從文化思想層面著眼,大力引入西方的各種現代觀念來啟發、教導國民,希望以外來思想解除國民精神深處因襲已久的傳統思想。換句話說,思想精神層面的解放是五四時期各種解放的重中之重,唯有刷新、重塑國人的精神世界,才可能為其他解放開辟道路。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思想精神解放是一切解放的前提,為了全心全力開展思想精神解放,有必要舍棄和擱置其他層面的解放。受以思想精神解放為主的思路影響,五四文學的“解放”書寫著重表現的幾乎都是進步青年如何在先進思想的提示下感到不滿,進而與代表封建傳統思想的老一輩進行抗爭。擺脫家族的拘囿,從思想上解脫出來,似乎就意味著一切。但擺脫、告別之后的故事則很少受到關注;被擺脫、被告別的對象怎樣在解放浪潮中得救,也沒進入作家視野。結果,解放只與“娜拉”們、“覺慧”們有關,與封建家長、守舊人物完全無涉;獲得解放后的“娜拉”和“覺慧”們也僅僅攜帶著樂觀卻單薄的思想勇氣闊步前行。五四時期的解放實質上屬于局部性的解放。被解放的“娜拉”和“覺慧”參加革命隊伍后,經濟物質層面的解放又獨領風騷,其他維度的解放則被冷落。解放話語為革命者獨占,落后分子與阻礙革命者如何同時被解放話語照亮,那時的文學作品鮮有涉及。
與局部解放相伴而生的是徹底解放。從解放的范圍來看,五四時期的解放屬于局部解放;從解放的程度來看,五四時期的解放又屬于徹底解放。由于民眾的舊習慣根深蒂固,舊思想總是在不經意間“魂兮歸來”,而且解放造成的新空氣中往往還遺留摻雜著不少舊傳統的因素,產生了不中不西、不新不舊、時中時西、時新時舊的矛盾現象。有鑒于此,梁啟超表示,要想完全刷新國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得造就一個徹底的大解放空氣:“既解放便須徹底,不徹底依然不算解放。”在“五四”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可發現由徹底解放觀念主導的情形。比如,巴金《家》中的覺慧因為擁有了“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的徹底解放精神,才能“逃出那個在崩潰中的舊家庭,去找尋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卻把年輕有為的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在革命進程中,徹底解放更是成了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選擇。20世紀20年代末,主持黨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必須徹底的實行土地革命,必須徹底的肅清封建制度的一切殘余”。進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明確規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是“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的制度,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農民(小私有者)要將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縛完成[全]摧毀”。之后,黨領導下的“左聯”在行動綱領中也作出指示:“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變成人類進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無產階級負起其歷史的使命,在這‘必然的王國’中作人類最后的同胞戰爭——階級斗爭,以求人類徹底的解放。”受徹底解放思想的影響,蔣光慈《田野的風》中的李杰在向農民宣講革命時,表達了改變“這窮富的制度”的徹底解放思想,并且堅決與自己的家庭決裂。
解放的面向千頭萬緒,受具體情形規約,往往需要讓某種解放“先走一步”。在這個意義上,局部解放的思路合情合理。但如何在社會改造、抗戰動員等語境中,掌控和平衡局部解放與全面解放、徹底解放與漸進解放的關系,使解放在范圍和程度上顯得適當,也是黨領導下的文藝進行“解放”書寫時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以家庭解放為例,20世紀40年代,黨的解放觀念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成功規避了只解放青年、無視老年,只解放個人、無視家庭價值的偏頗,適度且有效地解放個人和家庭,并促使其與革命斗爭形成同生共振的關系。舍棄家庭盡管有助于個體無牽掛地響應革命征召,但實質上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最佳方案應該是改造家庭,消除家庭負累,使整個家庭都支持個人的前進行為,甚至整個家庭共同投身革命。正是意識到徹底毀棄家庭、投身革命解放運動存在的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40年代盡管也主張把個體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參與到革命斗爭中,然而此時提倡的家庭解放已不是與家庭“脫域”的解放,而是“在家庭內”的解放。這種家庭解放是延安作家描寫的重點。
在唱本《春英翻身》中,與長工陳木祥結婚后的春英,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和啟發下,報名參加了婦女會,積極學習新文化和新思想。不料,婆婆看見春英成天不著家,就怒斥她,丈夫也站在婆婆一方批評春英胡作胡行、違背“婦人規矩”。后來婦女會會長對春英家人講了一番道理: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斗爭才讓他們翻身解放、過上了好生活,獲得解放后他們更應該積極參加革命,以便徹底驅除強暴,“消除痛苦過時光”。婦女會會長的話不僅掃除了春英丈夫和婆婆的舊思想,還促使春英丈夫和婆婆都踏進了革命隊伍,“陳母心頭多喜悅,亦跟婦女大翻身;木祥也去拿槍桿,當了民兵衛家鄉”。同樣,趙樹理《傳家寶》中的金桂對于婆婆的頑固阻撓,也不是簡單地進行批判斗爭或決然地拋棄家庭“出門遠行”,而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漸漸糾正婆婆的封建思想。《小二黑結婚》之所以被確立為解放區文學的重要收獲和創作示范,除了因契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大眾化的期許外,還在于其表現了二諸葛、三仙姑這樣的“落后的人物在斗爭的環境中也不能不起變化”,以及革命與家庭攜手共進的新風貌。
《春英翻身》和《傳家寶》的家庭解放是通過革命領導者或進步分子的訓教開導實現的,而在小說《黑牡丹》里,家庭解放則表現為革命政治威力作用下舊家長主動檢討的方式。《黑牡丹》講的同樣是一個解放的兒媳遭到家人反對的故事。錢蘭英僅僅因為在春節文娛大會上“出了風頭”,不小心跌了一跤,就被公公視為有礙觀瞻,遭到丈夫文玉的數落呵斥。深感委屈和憤怒的錢蘭英叫嚷:“今天非講理不行!”錢蘭英說出來的“講理”二字瞬間讓公公想起了政府領導的種種反封建舉動,想起了一系列像他自己這樣的老人“被講理”的場景,于是變得惶惑起來,準備主動到婦救會那里承認錯誤。丈夫也在妻子“講理”的正義聲浪中開始自我反思,并很快向錢蘭英做了檢討,夫妻倆最終和好如初。無論是領導者和進步者親自出面進行勸導,還是革命語境本身的刺激感染,中國共產黨解放觀念影響下的家庭解放書寫都呈現出重塑家風,進而使家庭與革命攜手共進的全面漸進式改造路徑。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家庭解放不僅強調青年一代向進步思想靠攏,還讓革命青年反過來感化、改造老一輩;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家庭解放不是以徹底、激進的方式拆解、分裂舊家庭,而是在漸進改造的思想指導下讓家庭關系達到新的和諧、平衡。中國共產黨的家庭解放達到的,正是在家庭內部感情融洽、在家庭外部工作積極的效果,融洽的家庭環境正是民眾積極從事革命工作的重要保障,革命工作又反過來時時監督家庭、不斷擴充家庭的和氣,兩者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禎祥”之景。如此一來,中國共產黨的家庭解放把“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聯系起來”,讓“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相互配合,既解放了青年一輩,也解放了老一輩;既解放了人,更解放了家庭本身。經由革命的塑造,家庭已非原來的家庭模樣,重回家庭的人也不再是呂緯甫那樣“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的哀苦之人,而是將革命引入家庭,以革命的力量全面解放家庭,然后又把家庭成功納入革命進程中的奮進之人。
與家庭解放相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成功推動的革命斗爭運動,也不是求簡、求快的徹底解放,而是根據具體時勢采取的有步驟、次序的漸進解放思想。在抗日戰爭期間,民族國家危亡問題統攝一切,反抗侵略成為頭等大事,于是中國共產黨便積極降低革命的調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盡量開展“交朋友”的工作。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力爭和平無效的情況下,開始加大對國民黨、大資產階級和農村地主階級的革命斗爭力度,最終“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此時期革命作家的“解放”書寫,配合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工作,遵循中國共產黨有步驟、次序的漸進解放思想而展開。
革命解放的關鍵是激發群眾的斗爭積極性,這就需要相信群眾、鼓勵群眾,不給群眾潑冷水。借用《暴風驟雨》中蕭隊長的話來形容便是:“害怕群眾起來整亂套,群眾還沒動,就給他們先畫上個圈子,叫他們只能在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而黨的革命解放思想又是漸進的而非激進的,當被發動起來的群眾提出一些超過政策限度的要求,民眾的徹底解放訴求和黨的策略性局部解放主張之間就難以協調。如何把發動群眾運動與引導群眾運動統一起來,怎樣做到既尊重群眾的斗爭要求,又使之走上正軌,黨的策略是“發揚群眾的階級意識,承認農民行動之合理,然后誘導群眾自己向地主讓步”。周而復表現減租減息運動的《山谷里的春天》,斗爭了地主“壞豌豆”徐紹堂,但最后也給他留下了適當的土地,使地主及其家人也加入到生產勞動的行列。在《桑干河上》中,斗爭了地主錢文貴后,農會查封沒收了村里地主的財產,但還是給他們留下了維持基本生存的家具、糧食和田地。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成功推行的階級解放運動絕不局限于經濟地位層面,而是多種面向齊頭并進的全面解放。無論是減租減息還是土地改革,階級解放不僅要減輕、消除封建剝削和階級壓迫,“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升貧苦農民的經濟社會地位,而且還要解放民眾精神思想內部的種種顧忌與落后性。《暴風驟雨》里第一次斗爭韓老六失敗后,工作隊員深入農民中間,與他們談往事、嘮閑嗑,強化了民眾的階級觀念,最終成功斗倒了韓老六。在評價這一勝利時,蕭隊長感興趣的是通過斗爭“由群眾來把封建堡壘干凈全部徹底的摧毀”。蕭隊長口中的“封建堡壘”既指以韓老六為代表的外部壓迫勢力,更指向民眾思想層面的封建觀念。前述以算賬、訴苦為主要方法而使民眾“翻心”的場景更是思想解放的絕佳寫照。
總之,黨領導的階級解放不僅從經濟層面為農民帶來了變革,更在精神思想上造成了一場全新的“革命”。人們在此過程中得到的不僅僅是土地、糧食與財產,“而是識大體、顧大局、守紀律等一整套新思想,新觀念”。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解放,官民同心的革命圖景得以樹立起來。黨領導下的文學以表現農民為重點的全方位的“解放”書寫,呈現了受壓迫者經濟提升、地位翻轉、思想重構及干部改造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解放觀念及書寫形態,規避了局部解放的不足,帶來了全面解放的燦爛景致。
結語:中國現代文學“解放”書寫的當下啟示
解放觀念是影響現代中國的重要思想觀念,甚至可以說,解放觀念是現代中國的主導性觀念,因為諸如自由、平等、民主、反帝、反封建等深刻影響和形塑現代中國歷史的思想觀念,無不受解放觀念的影響和促發,并可納入“解放”這一總體視角之下。因此,若要深入辨析、闡發這些觀念的內涵,不妨從“解放”這一主導性觀念和總體視角進入。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本文嘗試從“解放”這一主導性觀念出發,總體呈現中國現代文學與解放觀念的關聯互動。從解放主體、解放路徑與解放范圍程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形成了自我解放抑或被解放、說理式解放抑或斗爭式解放、局部徹底解放抑或全面漸進解放的“解放”書寫傳統。普通作家的解放觀念表達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態度,而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觀念及其影響下的文學“解放”書寫,則讓每一組中的兩種解放觀念形態交互作用、彼此融會,建立了“解放”書寫的新形態。
站在建黨100周年的重要時間節點上,回望和探索解放觀念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聯,在豐富我們對歷史來路的認識之余,也為當下和未來的文學“解放”書寫提供了有益啟示。
1.文學的“解放”書寫可為自由的生長開辟領地,也應給責任的出場保留通道。
毋庸諱言,中國現代文學的“解放”書寫經常與自由相聯結,現代作家之所以投入大量精力來思索解放、言說解放,很大程度上正體現了對自由發展的渴求。自由雖是現代作家稱許和珍視的寶貴精神,但中國現代文學的“解放”書寫同時也屢屢提醒人們,求取自由需要解除束縛,不過這絕不是毫無顧忌沖破一切束縛和滿足一己之私的借口。當五四時期以女性解放為代表的解放潮流出現濫用解放觀念的不良現象時,冰心提出了以責任意識作為補救:“我們一面要求解放,一面要自己負責任;否則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解放運動的進行,要受累不淺了。”沈雁冰為女性解放助威時,也注意到Right的對面是Duty,在力爭自由的權利之后,更得擔負增進國家發展的責任:“既然享受了人的Right,便該盡人的Duty。人的Duty,不只是衣食住,維持自己的生存;也不只是當兵納稅,做個所謂‘國民’;人的責任,一面要維持前代以及現代的文化,一面欲擴充他,增進他,傳給將來。”女性解放如此,其他各種解放概莫能外。呼喚自由與強調責任,應該成為“解放”書寫不可偏廢的兩個維度。
2.解放雖說要破除已有的禁錮,但尊重傳統和民眾習性卻是解放順利實現的基礎,因此文學的“解放”書寫應對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式思維保持警惕。
對于人類而言,傳統的規則、思想、制度乃至文化藝術是后來者能感受到的壓制性因素,所以解放往往以反叛傳統的形式展開。具體到現代中國,白話文對文言文的反叛,新文學對舊文學的反叛,個性解放對傳統順天安命和忠孝節悌思想的反叛,女性解放對傳統兩性關系的反叛,家庭解放對傳統家族制度的反叛,無不是打著反傳統的旗號進行的。乍一看,解放與傳統是一對天敵。可細究起來,最初為解放而發出的決絕的反傳統呼喊,很多時候只是一種策略性姿態,是想以“拆屋頂”的架勢達到“開窗”的目的。其實,對傳統的抨擊有時并非抨擊傳統本身,而是對利用傳統思想奴役民眾的做法表達不滿。例如,五四時期的“非孔”,主要不是針對孔子本身,而是針對被君主塑造為“專制政治之靈魂”的那個“偶像的權威”,即被當作帝王術的孔子思想。而且,“新命題從傳統的命題中尋找出發點,它們包含著許多從傳統中接受來的因素”。革命解放運動的順利展開,需要讓革命解放的觀念播撒到廣大民眾心中,其言說方式就得適合普通民眾的思維意識、生活習慣和話語趣味。因此,革命作家筆下便經常出現領導者虛心利用歌謠、快板、說書、戲曲等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文藝形式和語言形式成功推進階級解放的場景,通過維護家庭和睦關系來反哺革命解放運動更是延安作家和解放區作家傾心描摹的重點。不僅新的解放觀念的傳播可以利用傳統的文藝形式或民間文藝形式,而且,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的創構也可從傳統資源中汲取養分和靈感,以便做到推陳出新。這也提醒我們,文學在書寫和探究解放問題時,切忌把現代和傳統視作非此即彼的關系,二者的交錯中恰恰有著廣闊的表述空間。
3.不存在“畢其功于一役”的完全解放和一勞永逸的全面解放,關于解放的思考和書寫也將永無停歇。
作為一種總的觀念話語,解放包含許多具體類型,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所有解放類型齊頭并進,最終匯聚成解放勝利的大合唱。然而,因現實語境的限制,各種解放類型在實際操作中需要作出輕重緩急的區分,采取讓某種解放“先走一步”的思路。而且,某一類解放的具體實施過程,也是一個漫長的漸進之旅,不可操之過急。無論整體的解放,還是單一類型的解放,“畢其功于一役”的完全解放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丁玲、趙樹理等作家多次在作品中,讓革命領導者想方設法告誡、勸說、引導廣大民眾懂得并遵循漸進解放的道理,由此折射出中國共產黨充分考慮實情的解放經驗。“畢其功于一役”的完全解放設想并不可靠,一勞永逸的全面解放也是一種幻影。首先,解放的類型繁多,各個類型的解放有先有后。解放的類型有著歷史規約性,“‘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解放的觀念和實踐既取決于束縛和壓制的情形,也取決于解放者對這些壓迫力的認知程度,而壓迫力及對之的認知因時而變,這就推動了解放的不斷展開,也使文學的“解放”書寫不斷更新。其次,舊的束縛消失了,往往又會產生新的桎梏。例如,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圍困。最后,解放涉及社會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在不同歷史階段具有各自的特點。各個群體的權力關系、身份體認和經濟地位是相對的,在社會關系中處于弱勢、劣勢的群體難免產生被束縛的體驗和認知,由此在歷史的各個階段都會生發出解放的訴求。凡此種種,都證明解放是人類永恒的命題,是一條永無止境的漫漫征途。相應地,文學藝術對解放的思考、探究和書寫,也將永無止境。